亲爱的读者周五好,上周闲话了中国历史学家:
公平起见,这周闲话西方历史学家。
落到了坏人手里
在被渐冻症折磨的人生最后岁月里,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如此回忆 1980 年代的西方历史学界: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牛津大学教政治。有工作保障,有职业责任,还有个环境良好的家庭。婚姻美满自是不敢想的,不过我已习惯了不美满。
问题是学术上我不再投入了。
那段时间的法国史落到了不知所谓的坏人手里:社会史提出所谓“向文化转向”,出现了动辄“后”某某主义的潮流。新创设的“亚学科”迫使我没完没了地读些面向所谓学术精英的艰深冗长的文本,且这些学科信徒势力越来越大。
我感到了厌倦。
托尼·朱特《记忆小屋》中年危机篇
朱特这里指的是战后史学的一次重大转向:The Cultural Turn.
历史学家的兴趣飞速离开政治、社会-经济,转向文化;随兴趣转移的还有研究方法,文本和话语分析成为时髦的新工具;随工具迭代的还有史学观念,史学不再被视为追求真实,而是被解构为对抗的叙事。
学术兴趣的迭代有自身的动力:老一代历史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新一代想拓宽研究视野;世俗点说,至少能多发新论文。
学术兴趣的变化也可以放到社会背景中去观察:1968 年西方街头运动的左翼年轻人长大了,他们开始填满大学里的人文科系。新老师们高举文化批判的武器,以此反抗自己所生活的战后资本主义社会。
老一代学者相信战后民主重建的成就,西方民主 VS 东方专制。
新一代则重建一套新的压迫者—受压迫者叙事。在新故事里:教授们自己所生活的美国、法国和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才是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的破坏者,而真正的英雄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反抗者们。
丛林里的游击队员、远方国家的共产党领袖甚至解殖浪潮后的恐怖分子都披上了一层革命的浪漫外衣。
当头一记闷棍
1985 年,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余茂春赴美求学,他深知中国史学届缺乏研究自由的弊病,向往到自由的学术环境中追求真理。然而:
在我雄心勃勃,满怀浪漫主义情调踏上美国求学的 1985 年,迎接我的不是历史研究领域的潺潺流水之声,而是当头一记闷棒,砸得我头昏眼花,一时不知所措。
……
美国历史学界逐渐冷落甚至放弃了兰克(“如实直书”)的主张。在不少重要的研究领域里,“历史的客观性”早已成为带有讥讽意义的贬义词。
以美国历史为例,传统的史学强调美国立国的自由民主精神,认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如阶级和族裔,一到美国,就被美国的自由和平等淡化,因此,美国历史上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
这种传统的史学观当然会受到挑战,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基本上被彻底推翻。现在,美国历史系中如果有谁还把“大熔炉”当作美国历史的主流,恐怕是拿不到终身教授头衔的。
但是,“翻案史学”在很多方面走过了头,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由于过分强调冲突和矛盾,美国历史被弄得支离破碎,缺乏整体性。“翻案史学”中几个重要分支如移民史、黑人史、妇女史、印第安人史等等,互相之间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
《在美国发现历史》余茂春章节:西方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我在美国的学术生涯
最终余茂春选择“躲”到美国的军校里教书育人,文化批评在这里还不是主流;至少在美国海军军校,历史学教授依然可以称赞开国之父们的成就,不必过度强调他们作为“奴隶主”的压迫者属性。
大多数欧洲人毫不在意
挪威人文安立生于 1960 年,这位左翼青年在 70 年代末作为首批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留学,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冷战史学家。
他在新作《冷战》中甚至对自己年轻时的狂热做了一番自嘲: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毛泽东的文革狂热被叛逆的学生和其他人视为挑战自己国家权威的方式。中国的斯大林式的清洗因此有时候莫名其妙地与他国六零年代青年时代的反叛结合在一起。
其中一个最为奇怪的扭曲现象在西欧,有些知识分子组织了毛主义团体。他们认为可以同时崇拜毛却又反权威。例如,在富裕的挪威,学生组织了一个叫做工人的共产主义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论是中国本身或在国际上都前所未有地强大……(挪威)从未对中国的兴趣与情谊如此普遍高涨。”
但是即使有些知识分子欢庆中国的悲剧,大多数欧洲人却毫不在意,在选举中没有任何毛主义政党获得过超过 1% 的选票。
文安立《冷战》第九章中国的灾祸
就像文安立指出的那样,后 1968 时代狂热的左翼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只是社会中的喧嚣少数,他们在大学象牙塔里的人文科系中抱团取暖,一旦走向社会面对公众常识和选票箱子的检验,立刻就现出了奇怪扭曲的面目。
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文化史转向是从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史观三个层面同时发生的复杂转型。
认同应该进行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未必认同以文化批判为主要方法;使用文化批判方法的人,未必认同激进左翼的全部理念。
同时西方学术界是多元的论坛,各种流派和研究方法碰撞。
文安立个人的学术历程是个范例,一个真诚的左翼青年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学习中文,最终走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反面:成为一位具有广博国际视野的史学家,他亲手揭掉了对东方共产主义的浪漫想象。
为何发生这种转变? 因为他不再远远坐在西欧都市里看电视、读书、与同好抱团,而是真的来研究中国究竟发生过什么。
理性前进的地方,幻象迅速消散。
托尼·朱特如何走出的职业危机?
朱特转身背对 1968 的巴黎时尚,选择拥抱 1968 的布拉格精神。他开始学习捷克语,研究中东欧。
我开始教授东欧历史,并——诚惶诚恐地——书写它。
换言之,学习捷克语使我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学者、不一样的历史学家以及一个不一样的人。
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我便不会于 1989 年 11 月置身布拉格的城市广场,从阳台上亲眼看到哈维尔荣登总统之席。
最重要的是,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我也不可能把自己从 1945 年以降目睹的欧洲史写成《战后欧洲史》一书。
我这个中年危机,大约是所有中年危机里最好的一种。它根治了我身上后现代学院派方法论至上的毛病。
不管怎样,它也在客观上使我成为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共知识分子。天地之大,比西方哲学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出很多,而我窥见了其中的一部分,虽然这一刻姗姗来迟。
托尼·朱特 《记忆小屋》
进一步阅读
这篇只是闲话,没有对任何历史学家和历史学流派不敬的意图;并不是要否定整个文化史研究,仅仅闲聊一下文化转向中的泥沙俱下。
文中所引用的批评,托尼·朱特是一位左翼的社会民主人士,余茂春是美国右翼保守派,他们站在不同的视角,却各自独立产生了对激进文化左翼的共同批评。
这篇聊的是 1980 年代的西方历史学界,无意影射当前欧美大学的人文学科教育。目前情况是更好还是更糟了,有待亲爱的读者们自行判断。
我有读文化史的书,听文化史教授的课,学习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并从中受益良多,未来期待能阅读更多杰出的著作。
同样一篇小小的闲话也不可能讲明白战后史学史,如果感兴趣,可读入门书 何兆武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文中提及到的图书:
托尼·朱特 《记忆小屋》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文安立《冷战》
感谢您的阅读,如果喜欢请推荐给家人朋友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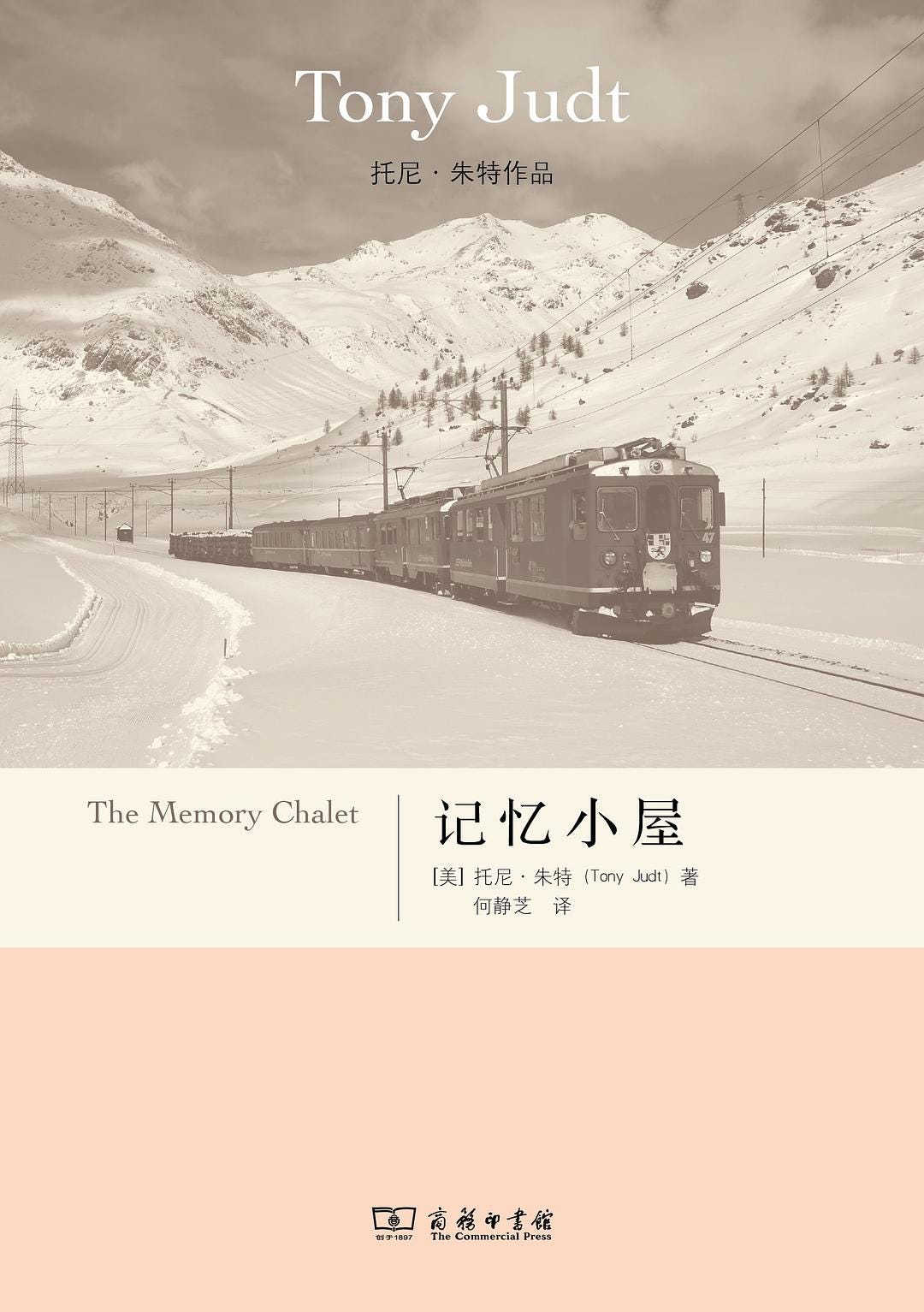
这篇写得真的好。
《在美国发现历史》的引用部分最后一段,“由于过分强调”写成“由子”了。看来是自己手打或者ocr的?作者幸苦了